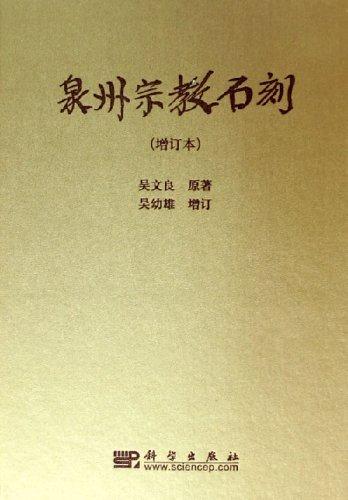| 吴文良吴幼雄 与 泉州宗教石刻 |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
|
宋元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评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的《泉州宗教石刻》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 第3期 林振礼
《泉州宗教石刻》这一重大选题,20世纪50年代就得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的重视和支持。吴文良先生业余考古,于1957年出版了原著,实有筚路之功。增订者吴幼雄秉承并超越其父“以物证史”的治学路径,对书中有历史意义的碑文,做了精辟的考论,其中不乏深达幽微的洞见。该书的出版,为泉州及其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
吴文良父子的“爱石说” 讲述泉州宗教石刻故事 2013年04月22日 09:29 来源:东南网 记者 林继学 谢向明
谁是中世纪“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最好的见证者?是泉州大量的宋元石刻。譬如记录了泉州航海祈风典礼的九日山摩崖石刻,它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证物。这些曾饱经风霜,或遭遗弃、或被践踏的宝贵石刻,即将成为一部纪录片的主角。这部纪录片,近日由鲤城区宣传部与开元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紧张筹拍,讲述泉州宗教石刻,及爱石人吴文良父子收藏、保护、研究石刻的故事。如果进程顺利,它将于第二届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推出。
泉州宗教石刻考古专家吴文良、泉州著名文史专家吴幼雄父子俩,对这些石刻付出了极大心血。
吴文良家在泉州县后街,生于清朝末年,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当年,听取了两位考古学家张星烺和陈万里关于泉州考古学术的报告后,吴文良放弃生物专业,选择考古学,开始了一生的考古钻研。毕业后,他回到泉州当中学老师。
业余时,吴文良喜欢搜集和研究,古代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各国人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想解开中古时期泉州与海外各国的海上贸易、文化交流。
生性豁达的吴文良因为收集宗教石刻,交友甚广。1932年后定居闽南的弘一法师,就常到吴文良家拜访。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合适,廓而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1942年10月,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后,留下的这副遗偈成了吴文良与弘一法师等宗教界朋友坦荡心胸的写照。
抢救多处石刻 填补海交研究空白
九日山的摩崖石刻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证物。
吴文良曾在《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里写道:“因年代久远,苔藓封翳藤葛滋蔓。且刻字的摩崖石刻岩石均极高大,刻工又深浅不一,风化相当厉害,非用云梯攀登,仔细刮爬,字句每难辨认。”他多次爬上九日山,仔细校对摩崖石刻,详细考证石刻的时间、作者,为我们还原了这些被忽视的财富。
如今,镶在涂门街清净寺门楣上的那方石刻,也得益于吴文良的抢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吴文良在泉州德济门城墙拆毁时,发现了这方完整的石刻,上面写着他读不懂的阿拉伯文字。苦于付不起45美元,吴文良找到清净寺负责人,劝清净寺收购。
吴文良花了一生的时间,撰写了《泉州宗教石刻》,引起了学术界,乃至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著名考古专家夏鼐曾评价吴文良是“填补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空白的人”;当年,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时,还特意向吴文良要了8本《泉州宗教石刻》。
1969年,吴文良离世。儿子吴幼雄继承了父亲的信念,继续宗教石刻的考证、研究,进一步完善《泉州宗教石刻》,并于1991年再版。
父子两代人,花了78年的时间,才完成这本专著,为泉州地方史及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泉州草庵寺---世界现存惟一摩尼教寺庙遗址
摩尼教的转世生命:从救世到捉鬼 2007年08月26日13:51 厦门网-厦门晚报
草庵寺前出土的写有“明教会”字样的黑釉碗 草庵寺里的明代摩尼教石刻,如今成了驱魔咒语。
弘一法师的误读
喜欢草庵,最主要因为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座摩尼教寺院。还因为弘一法师生前也十分喜欢这座寺院。去年夏天,我与朋友陈飞鹏一起去草庵。有位80多岁的老“菜姑”,声称自己见过弘一法师。飞鹏高兴得很,当即用摄像机采访了起来。
今年初,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约我一起去草庵,他说晋江博物馆的粘良图先生发现了摩尼教的一些变异形式,很有学术价值。这样,我们一行三人,就去了草庵及附近村落。
到了草庵,我说起上次见到的老“菜姑”。粘先生说她已经去世了。她原是童养媳,不识字,只会念阿弥陀佛,从小就在寺里做些粗活。文革时红卫兵要砸摩尼光佛,她指着省政府立的重点文物保护碑,要他们先砸碑,再砸佛像,那些人不敢先回去了。她连夜用黄泥糊掉了佛像,才保护下来。
弘一法师非常喜爱草庵。1933年、1935年和1937年三个冬天,他都呆在草庵度岁。他住的意空楼已经不存,但他为草庵留下了不少精美的书法,犹留存于柱壁间。
当时,草庵只是一个清静的佛教寺院。法师写过一篇《重兴草庵记》,其中云:“草庵肇建,盖惟宋代。逮及明初,轮奂尽美。……殿供石佛,昔为岩壁,常现金容。因依其形,雕造佛像。余题句云:‘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载记,于此有名贤读书。’盖记其事也。”
这段文字,证明弘一法师还不了解草庵的真实历史。他把石壁上雕刻的摩尼光佛错误地当成佛教的释迦牟尼佛了。这很正常。摩尼教已经湮灭三四个世纪,早已被人遗忘。
草庵被识别为摩尼教寺这一重大发现是泉州宗教考古学家吴文良先生做出的。1957年他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中公布这一成果。1961年,草庵被列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8月,在瑞典举行的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会议上,各国学者一致认为草庵是世界现存惟一摩尼教寺庙遗址。1996年,草庵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草庵原本是摩尼教的寺院
草庵是我到过的最漂亮的寺院之一,清幽,别致,精巧。没有一进又一进的大雄宝殿,没有一尊又一尊大同小异的佛像。草庵的核心是一尊岩壁上凿出的浮雕佛像,为这尊佛像,建了一幢三开间的小石室。其他,都是附属设施。
这尊佛像与所有其他佛像都不相同,它是摩尼教这个已经消失数百年的世界性大宗教留存至今的惟一雕像。根据题记,我们知道雕像完成于1339年,那时是元朝,附近村落一位陈姓施主为了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而出资雕造的。
元代的草庵无疑属于摩尼教。《闽书》还记载说:“泉州府晋江县华表山……山麓有草庵,元时建,祀摩尼佛。”在晋江博物馆,我们看到了一些草庵寺前发掘的黑釉碗,上面写着“明教会”三字。据考证,这些碗属于宋代磁灶大树威窑所烧制的产品。也就是说,草庵很可能宋代就是摩尼教的寺院了。
摩尼教是唐前期从中亚传入中国的,历经唐宋元三代,风风雨雨,波折不断,总还一脉相传。到了明初,因为明教的“明”字上逼国号,朱元璋严禁传习,毁其宫室,遣散教众。对摩尼教来说这是一场灭顶之灾。然而,偏远的福建摩尼教还坚持了一阵,因为半个多世纪后,草庵又多了块摩尼教石刻:“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乙丑年九月十三日”。落款的纪年为公元1445年。可见摩尼教的草庵还没有失守。
又100多年过去了,草庵不知怎么成了道教的地盘。明万历年间(1573-1620),惠安诗人黄克晦游草庵,说是“结伴遥寻太乙家,峨峨万石映孤霞”(《万石峰草庵得家字》);泉州诗人黄凤翔眼前也是一片荒芜:“竹边泉脉邻丹灶,沿里云根蔓绿藤”(《咏草庵》)。“太乙”,“丹灶”云云,看来他们都把草庵当成道观了。
再后来,草庵成了佛教的寺院。1923年,瑞意和广空法师筹资修复草庵;1932年,在殿堂东建成意空楼。弘一法师就是这时期来到草庵的。
摩尼光佛的胡须
草庵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那尊摩尼光佛雕像。石壁上凿出的一个圆形佛龛内,面相丰满的摩尼佛宽袖僧衣,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背景是十八道放射状光轮。因为石质不同,佛像的脸呈草绿色,手粉红,身灰白。最引人注目的是,佛像两肩各散下两纽黑发,颚下垂下两条长须。
摩尼佛像世所罕见,可以比较的惟有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吐鲁番发现的一幅摩尼壁画像。那是唐代西域回鹘族人的遗物。其形象为:“高僧衣白法衣,胸前有绣纹,左肩缀阔绣带,帽施金绣,颈间系黑纽,面长圆,鼻作鹫形,目小而歪,酷肖中国人描写欧人之手笔。其背光为新月及太阳,新月作黄金色,太阳作淡红色。”(《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
对照看,二者的差异很大,最大的差别是:吐鲁番壁画的摩尼像有冠,无须;草庵摩尼雕像无冠,有须。
吴文良先生认为,草庵的摩尼光佛雕像,和释迦牟尼佛造像大不相同:释迦造像多雕塑成慈眼低垂,鼻梁高畅,双颊圆润,且头上有螺发,下巴无须;今日在草庵所见的摩尼佛造像,无螺发,而有两道长须,垂至腹际。其背后的光轮,也和释迦牟尼背后的佛焰不同。
佛像无须,道士有须,这是我们一般的认知。蔡鸿生教授因此说泉州摩尼光佛雕像的特征是“佛身道貌”。林悟殊教授认为:“这一形象是摩尼教在中国这一佛教、道教为主流宗教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嬗变的产物。”他们认为,摩尼的形象,在历史中逐步演化,吸收了本土佛道两教神像的特点,才变成这种形象。
然而,关于摩尼光佛的胡须,粘良图先生另有新解。他说摩尼光佛本来就没有胡须,是上色的人上错了,因为石壁上没有胡须的刻痕。还有,他认为头发也上错了色。每边本来各有三纽头发垂肩,可是两肩最外边那纽头发没有上成黑色,却上成了红色,结果每边只剩两纽头发垂肩。
如果这样,摩尼光佛的胡须就是一个假问题。许多争议压根儿是观察疏忽造出来的。
民间的“摩尼公”
在草庵附近的村社里,民间还保存着一些摩尼佛像和祭祀仪式。这就是粘良图先生近年来的重大发现。
午饭后,他带我们去东石。东石是靠海的港口,距草庵约20公里。在玉井户夫子馆(即关帝庙),几位老妇人正在打牌。说起“摩尼公”,她们领我们去看配祀在左边的两尊小神像。其中黑脸的有100多年历史,当地人又称“番仔佛”,功能是保护海上平安。红脸的较新,模样相仿。两尊神像都是头发分垂双肩,每边三纽,下颌无须。
庙里的老人说,摩尼公驱魔赶鬼最灵。每年神诞前一晚,都要请神去草庵陪佛过。他们自认草庵是摩尼公的祖庙。
草庵下面的村子叫苏内,民间也有“摩尼公”神像。村里的五都水尾宫很新,有摩尼光佛、秦皎神使、都天灵相等。但三神都已被人请走,只剩下画像。村民说,三神的祭品都只用素菜。每年农历6月13是摩尼公的生日。就我看来,这里描绘的摩尼光佛壁画,显然抄袭自草庵的浮雕。村民说,附近一些村子也有信摩尼公的,但不如苏内村。
粘良图又带我们去村里的曾天法(已去世)家。他说这家人祖祖辈辈都做乩童,他们家传的摩尼公像,为苏内村已知的惟一一尊。因为是私人的,就不必每年都去草庵割香,分炉。他家的摩尼公主要为草庵的摩尼光佛代言。
曾天法家的摩尼公造型古朴,与草庵雕像有很大差异,不但来历久远,显然还另有所本。神像头发分梳两边,扎了辫子,双肩各垂下两纽头发,无须。华丽的服饰有点像道士装,上面却写有“佛”字,盘腿在莲花台上。
我们见到的民间这三尊摩尼公神像都没有胡须。因为吴文良先生半个多世纪前见到的摩尼光佛就已经画错胡须了。如果民间的摩尼公神像是半个世纪内新塑的,源自草庵,那么也该有胡须。我相信,民间的摩尼公形象很可能另有自己的神像谱系。
驱魔赶鬼的符咒
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宗教,摩尼教的教义博大精深,它的目的是拯救灵魂,重建宇宙,让信徒的生命奔向光明王国。普通人热衷的算命、驱鬼之类迷信活动,是不屑为的。不过,自从摩尼教变异为民间信仰,就放弃了高远的理想,忙于俗务了。村民们异口同声说,摩尼公的最大本领是驱魔赶鬼。
粘良图又找来了曾天排,一位五十多岁的村民,长得干瘦。他也做乩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他介绍说,赶鬼要念咒语,比手印。所谓咒语,他透露说就是明代刻在草庵石上的那句话:“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这里说明一下,明代的摩崖原刻已毁,幸好吴文良先生著的《泉州宗教石刻》留下了照片。如今的石刻是根据照片重刻的。
曾天排说,咒语从前很灵的,谁念都灵。后来有位富人,倒尿盆的时候也念咒语,从此就不大灵了,还要配合手印,需要专业的乩童来做。
在我们的请求下,曾天排示范了手印:前五指张开,意为五指山;后拇指食指成环,其余三指竖立,意为三尊佛(佛教的西天三大佛)。比手印的同时,口中要念动咒语。
郭志超教授认为,摩尼公赶鬼,早在摩尼教还没有变异为民间信仰的时代就开始了。五代徐铉的《稽神录》里记载泉州杨家闹鬼,请来巫师作法,没想到鬼技更高,巫师落荒而逃,后来又请“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因而遂绝”。可见五代时摩尼教已经相当中国化,像道教一样装神弄鬼。不过这不是主流。明末摩尼教消亡后,才完全沦落为驱魔赶鬼的民间法术。按成书于明末的《闽书》记载,“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可见明末晋江的摩尼教已变异为民间信仰,继续流传。
我们没想到民间信仰的力量这么大,400多年后,这些符咒还在流传,不绝如缕。
应该怎么说呢?摩尼教死了吗?作为一门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宗教,它的确死了;然而它又没有彻底死去,它以一种更低级的形式——作为实用的民间方术——还在苟延残喘。世界之道,循环往复。曾经雄辩滔滔的宇宙学说,终极关怀,如今沦落为乡间捉鬼的符咒,让人感叹不已。
-------------------------------------------
关于明教与印度教湿婆派
公元前一千年前,由波斯雅利安人文化与印度达罗毗荼人文化相交汇后产生的古印度灿烂的吠陀文明,后来,吠陀文明演化发展为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而在印度教中,有湿婆派,梵天派,毗湿奴派。
吠陀文明最古老的经典是《梨俱吠陀》、古波斯最古老的宗教经典是《阿维斯塔》,波斯的这种宗教叫做祆(音仙)教,曾在中国曾有广泛的信徒,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安禄山和方腊都是祆教徒。而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著名的明教,其实是由祆教发展而来的摩尼教。中国民间称之为“吃菜事魔”(吃素食,但做事过于极端)。
祆教因为供奉圣火坛又被通俗的称为拜火教,在祆教圣经《阿维斯塔》中间,有17章的赞美诗,被认为来源于更为古老的波斯语,而正是这部分内容,几乎都能在古印度的《梨俱吠陀》中找到对应文本,除了一些发音不同,几乎没什么区别。
学者威廉.杰克逊在1892年出版的《阿维斯塔语语法与梵文比较》一书中,曾举出了一段阿维斯塔中的密特拉神颂辞与《梨俱吠陀》的内容相比较,即使对两种语言都不懂,也不难看出二者到底有多像: 《阿维斯塔》: tam amavantam yazatam suram damohu savishtam mithram yazai zaothrabyo 《梨俱吠陀》: tam amavantam yajatam suram dhamasu savistham mitram yajai hotrabhyah 汉语翻译:这是强有力的密特拉神,是所有创造物中最强大者,我谨以酒献上。
中国的元代文献中未发现有关湿婆教(印度教湿婆派)的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发现元代湿婆教雕刻遗物共200余方,特别是近年来屡有新发现。1984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附近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57×22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迭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塔状磨盘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势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破坏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破坏之神,但也有创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五十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到类似的龛状石。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发现得不少。
由此可见,吴文良收集到的湿婆教龛状石与吴文良识别发现的摩尼教草庵,其实都有精神上的共同的祖先--古波斯的经典《阿维斯塔》与古印度的经典《梨俱吠陀》的编创者―――伊朗-雅利安人
|